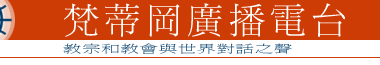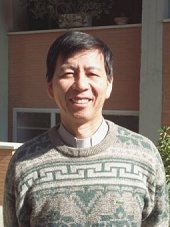|
|
|
29- 03-
2004 新聞報導 資料庫
東南亞通訊
-再談談「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陳日君 再談談「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陳日君 (一)劉先生說「公眾看到的圖畫是政府和立法者千方百計地遷就辦學團體,確保辦學團體日後對其屬下學校的校董會有充足的控制權」。不錯,這是政府宣傳機器砌出的圖畫,事實是法團校董會將取代辦學團體,也就是說在校董會及政府之間再不會有辦學團體的實質介入,也就是說政府將架空辦學團體而直接管制校董會。 政府事先並無諮詢有關團體,現在一刀切,強橫堅持推進這絕不「溫和」而有「革命性」的新法例(「天翻地覆」、「絕無後路」是當時教統會主席梁錦松先生推出有關諮詢文件時用的詞)。新人新政策毫無解釋地廢除「出籠」不久的教統會七號報告書,否定多年來與辦學團體的夥伴關係,我們會抗議到底,因為這絕不是教育制度的進步! 劉先生刻意強調我們所要求的「校監」的權力,其實校監只是辦學團體的代表,在他背後有主教、有主教代表、有龐大的中央校董會,有由校長級人馬組成的教區教育辦事處。可惜,按新例法團校董會直接向政府負責,這些教區中央的支援組織再有什麼名堂能插手幫助個別學校呢? (二)政府用「校政民主化」來掩飾這集中權力的企圖,誤導了很多善心的人。我們絕不反對「民主化」或「校本管理」的精神,我們非常贊成讓教師、家長、舊生更多參與校政,但七號報告書建議的校政執行委員會不是很好的方法嗎?而且不少辦學團體已主動邀請教師、家長參加(現行制度中的)校董會,鼓勵多些學校這樣做不是更好嗎? 我們反對「正式選舉代表」的規定,因為這樣做會製造新權力中心,使學校的運作政治化。在廣大社會中選舉可能是唯一辦法來匯集民意,但教育團體需要和諧的氣氛,大家認同辦學理念,同心合力,教育下一代,絕不適宜把社會上的政治分歧帶入學校裡。 (三)劉先生好像不相信「一位強烈反對辦學團體辦學理念的老師或家長可以將校董會搞到天翻地覆」。有機會我想和他分享49、50 年上海教會學校的經驗。 至於「每當校董會內有分歧,政府會派員入駐校董會」是新法例內的明文規定。就算「以為政府樂意這樣做」是陰謀論,也和我所說不屑置評的政治算盤拉不上關係。我的陰謀論有理據:政府用新法例為自己製造許多現在不存在的麻煩實在費解,社評卻把教育改制的問題和政治利益的衡量拉上關係,實在不屑置評。 最後我想問劉先生:我們接受政府資助是政府賜給我們恩惠或是我們義務幫助政府履行他的教育職責? 義筆容辭,回應徐錦堯神父 該書出版後,馬上引發出徐錦堯神父著文批評。本來,持不同看法的人都有發言的自由,我們尊重徐神父的言論,但我們認為批評按客觀事實及理性才有意義。徐神父對本書所揭發的資料,並沒有半句指出錯在哪裡或資料不正確的地方,反而一動筆就不滿正委「這樣看中國」,「籠中的鳥兒」這個概念充滿偏見和貶義,對中國不公平,也會被敵視中國的人利用去更敵視中國……云云。我們覺得這對正委不公平及以偏概全,有必要作出澄清--這不只是為了回應徐神父,更重要是我們不想因此被人扭曲了出版的原意。因為國內教友同胞在信仰方面所受的種種禁制,為在一國兩制之下的香港教友而言,首先我們有知情權,另方面他們在逆境下所表現出來對信仰的忠貞,更是對普世教會的見證。若因是次批評而令讀者看不到有關內容,我們實在感到非常可惜! 本書其中一個主要部份是由專注於宗教研究的學者親自撰文評述,亦有國內廣州石室的譚天德神父分享信仰經驗及再一次審閱個人的訪問稿,難道他們對國內教會的認識也會少嗎?再者,在中國,打壓教會的行動並不是個別事例或是零星地發生,而是每年都大量地出現,不少人也知道甚至親自目睹。故此,雖然我們與這些被捕的主教、神父素未謀面,但這絕不能成為我們迴避報導的藉口,特別是當這些事件已經被廣泛地報導,又有可信賴的途徑可以反覆查證、核實時,我們更不能用「不熟悉中國」、「沒有在中國生活」、「沒有深入接觸」為藉口而將兄弟姊妹的痛苦視為無物。 我們不否定國內不同地區在宗教政策上有不同的寬鬆度(這在本書中也多次提及),但是另一班弟兄姊妹確實承受著痛苦。當我們看河北省蘇志民主教、安樹新輔理主教竟然可以「人間蒸發」多年,范忠良主教、曾景牧主教等已是古稀之年,仍得不到片刻的安寧;浙江省姜溯念神父只因為印刷逾十二萬冊聖歌本,就要無辜坐牢達四年(原被判囚六年,後獲得提前釋放)。當看到當局採用的打壓手段及騷擾方式竟然如此不文明這一切,我們著實感到很憤怒、很悲痛而覺得有更大的需要去指陳出來。 本書從沒有「就是這樣看中國」(用徐神父語),恰恰相反,本書一個主要目的是要幫助讀者從不同層面認識宗教自由問題,打破有些人一些既有的想法。例如:在分析國內教會受到壓制的原因時,我們也帶出除了政治原因外,還包括經濟原因、官員的質素及監察問題(有關這方面中國領導人自己也曾多次強調),這正是想讓讀者知道宗教自由問題涉及多個層面,不能簡單地以一句「沒有宗教自由」就可以概括;在談到地下教會時,我們也指出它不是鐵板一塊,另外為了令教友不要誤會只有地下教友才受苦難,我們也指出了一些公開教會所面對的壓制。還有其他例子,在此不作詳述,我們深切希望徐神父不要以「既定的眼光」來看正委出版的刊物。 我們在此不想與徐神父作出爭辯而令本書的焦點被轉移了。其實,香港與國內教會交流頻繁,很多教友對國內宗教自由的認識也很豐富,故此,究竟本書的內容如何,讀者自可去判斷。我們希望有更多教友能夠分享出他們的經驗,以豐富香港教會對國內宗教自由的認識。因為畢竟報導、分享並不必然就等同助長敵視中國。即使我們有所批評,也都是針對政策,以及政策的制訂和執行,希望國家的領導人合理和公平地還給人民該得的尊嚴和權利。 我們相信,宗教信仰自由應屬於社會上每一個成員,一個社會若只准一小部份人享有信仰特權,就是畸形的現象,也是社會發展的悲哀。最後,我們認為宗教信仰自由不是政權的恩賜,也絕不能任由掌權者操控或隨意地為自由設定範圍。宗教信仰是每一個人的權利,人人生而擁有。雖然本書所紀錄的是天主教會的情況,但只是一個起點:我們希望國內的每一個宗教團體,只要它不使用暴力、不破壞公益,就有權利自由發展。讓我們共同為此祈禱!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網頁:jpcom.catholic.org.hk 韓大輝加入國際神學委員會 教廷三月公布的委員名單共廿六人,當中多是神父,包括四名來自亞洲的神學家(包括香港、南韓、印度和黎巴嫩)、兩名婦女(一修女和一平信徒)和一名男平信徒。 獲委出任委員的韓大輝神父為慈幼會中華省省會長,於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任教教義神學。韓神父獲羅馬慈幼大學神學博士學位,是亞洲主教團協會神學顧問,宗座神學學院院士。由於韓神父截稿前不在港,本報未能接觸韓神父。 「國際神學委員會」成立於一九六九年,負責研究重要的神學議題,並向教宗和信理部提供意見;委員會近年就執事、基督徒過去幾個世紀的過失,以及宗教交談發表文件。(植) 2004 年四月生活聖言 路加福音曾多次描述門徒們討論誰是他們之中最大的(參閱路 9:46),但這次卻在耶穌的最後晚餐中。那時,祂剛剛建立了聖體聖事。這件聖事象徵著耶穌最大的愛情,祂毫無保留地為我們付出自己,並在幾個小時後,在十字架上接受死亡。耶穌在門徒中間「卻像是服事人的」(路22:27)。事實上,若望福音卻記載了耶穌為門徒洗腳的具體行動。在這個月裡,當基督徒慶祝耶穌的逾越和復活時,緊記祂這方面的教導是很重要的。 「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人的。」 這是耶穌的生活所帶來的矛盾之一。唯有當我們認同愛是基督徒特有的生活態度時,我們才能明白這一點。這份愛驅使基督徒甘居末位,在人前變得渺小,就好像一位與幼兒玩耍嬉戲、與長子溫習功課時的父親一樣。
「你們中最大的,要成為最小的;為首領的,要成為服事人的。」 因此,我們應該「為他人而生活」,不要只為自己生活,不要只顧自己的煩惱、自己的憂慮、自己的想法及一切屬於自己的東西。 盧嘉勒
|
|
|
||||||||||
|
||||||||||